38年前,我把镢頭交給北灣林場,來到舞鋼首府文化單位,填報到表。表格有“個人特長”一欄使我犯難。我把江南毛竹和平原泡桐引植北灣,北灣呈現出奪目的園林氣象,林業(yè)部攜北京電影制片廠將其輯入科教片《綠化祖國》,在全國播映。1981年4月19日《人民日報》有消息報道:《綠化祖國》被評為1980年度優(yōu)秀科教片。但我若將種竹種樹填入“個人特長”欄中,接收單位會輕松而幽默地說:“此處不是大山,也沒有镢頭,非你用武之地,請另高就。”那么我又不敢妄填什么“文學創(chuàng)作”。我與文學絕緣20多年,早已提筆忘字。而我那個所謂“青年作家”的光環(huán),其根底只是讀一本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,又讀一本《小二黑結婚》;古典和歷史,一知半解;也不知哲學美學為何物。只知編故事圖解政策,配合中心工作(如三夏、三秋、變冬閑為冬忙這類),緊跟,快跟,從54、55、56,圖解到57,完了!我這等成色,讓我來輔導全市文學創(chuàng)作,能立身嗎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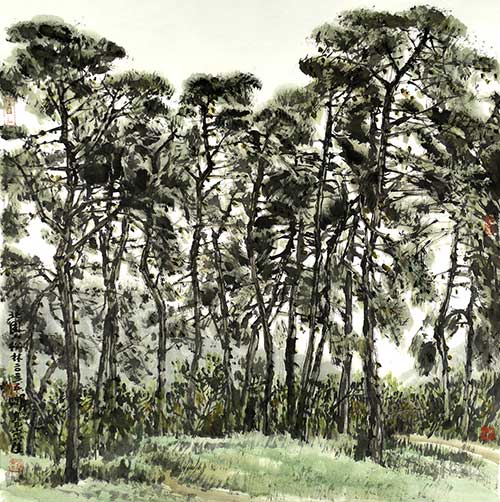
當晚,林業(yè)局李局長來見我,我向他說了苦衷,求他給拿個主意,他說:“要不,你還回北灣吧,北灣也真需要你!”我把李局長的話告訴妻子鳳蓮,鳳蓮說:“大山里沒學校,孩子們就當文盲了。”我說:“當文盲咋啦?跟咱一起挖樹坑的山民朋友,不都是文盲嗎?”我說這話,倒吸了一口涼氣。人有想得開的時候,也有想不開的時候,若遇上親友書香人家,能不比嗎?從面情到心境,何以堪?兩天里,我穿著林場工作服,戴一頂大草帽,在埡口街心,歧路彷徨,不知去從。
幾天后一個中午,我接到省作協(xié)常務副主席龐嘉季老師 一封信,還有一包書。信上說:“稼生你還年富力強。山上風景,紙上文章,你可以在稿紙上種竹種樹……”信末告訴我:“下月《奔流》開筆會,擬請你來。”這之后,陸續(xù)給我機會,到川陜、云貴、兩廣、湖南湖北等地,增多見識,又參加各種筆會、文學講習班。高密度高強度促我文思復萌。我像是嘉季老師手中正在搓捻尚未打結不敢松手的麻繩,迫不及待,又親自來到我家,促膝談,鼓勵再鼓勵,唯恐我畏難而退。
像當年接過林場韋福聚老場長的镢頭,我又從嘉季老師手中接過久別的筆。那時我已到了人生的“立秋”節(jié)令了,該是收獲季節(jié)了,而我還沒有播種哩。不敢怠慢,應當努力,應當十分努力!
自知時間不夠,不能一一閱讀中外巨著。就抄小路走捷徑。那時連環(huán)畫小人書盛行,尤其車站隨處可見,我趁出差候車,掏兩毛錢可以看半天,一部部長篇梗概,快速地進入我的腦海。其間被畫家省略的細事情感,將心比心,用我個人情感融入其中,使我因感動而受益。也是自己感動了自己。這種不完善的閱讀為他人所不取,但對當時的我,還屬最佳選擇。
我相信杜甫從“萬卷”中提煉了純屬于杜甫自己的語言。所以我得空就大聲朗誦唐詩宋詞元散曲;唐詩宋詞元散曲,風神萬種,在我口中發(fā)酵,量變質變,情理升華,釀出的,必然是自己的語言,不會有“雷同”之蒼白,更不會有“抄襲”之污痕。寫文章是教人懂的:口語親切,口語懇切,口語無隔,直抵人心。《論語》《孟子》《世說新語》,尤其詩詞散曲,其口語成分豐富,細心吸納,可心合意,構筑自己的風格,比起抓耳撓腮的做作,既快樂,又快捷。沒時間寫傷痕文學,傷痕文學太繁瑣,寫來寫去就那么個“冤”字;也不寫風花雪月。也不無病呻吟,有病也不呻吟。
只寫“要緊”的!
當我集夠《海藍海藍的眼睛》書稿時,嘉季老師審閱完剪報,興高采烈為我作序《依舊是心田上的好春色》。嘉季老師寫下這個題目時,一定是一臉喜悅,是種瓜得瓜的那種喜悅。
再回頭說:38年前,如果沒有嘉季老師那一封信,我們便返回北灣了,成為一個系列文盲家庭。女兒林杰在山中隨俗成家,吃飯過日子。兒子楊凱也許會有個女兒,也許也叫田田;但不會是今天這個能為爺爺文章插圖的田田。女兒也無從為我編輯《兩岸書》《北灣》《叩問童心》。
38年了,與海內外讀者和編輯的情分越結越厚,喜出望外,陽光燦爛,使這個寂冷的家不再寂冷。女兒在《北灣》的明亮處制了一枚紅色篆刻“文學救贖了我”。文學賦與我們這個家庭以新的生命。讀者信函電話不斷,春秋假日來家,穿堂過室,親如家人。遠在北美的《世界日報》把《叩問童心》連載完畢,責任編輯桂文亞成為我家的朋友,給田田還寄過壓歲錢,她退休10年了,仍有信函往來。林杰稱她為桂姊,田田稱她桂阿姨。
嘉季老師1979年第一封信是播種,種籽播入田中。爾后,他必然是一個“守望”者,守望種籽發(fā)芽生根、成長抽穗,于是,他必然又是一個“收摘”者。一穗一穗地收摘我的剪報,使他喜悅,所以給我頻頻寫信,已不止200封,加上電話這有聲的信函,已是不計其數了(我已將其放入一個小木箱中,木箱上寫著“嘉季老師的信”)。2016年1月23日收到老師一個很大的郵包:內有兩個大袋,一袋是他收存我的歷年的剪報和別人的評介剪報,袋上注明“稼生文稿”;一袋是田田的畫作。還有一套6本新購的散文名家經典著作。還有一個信封,內裝一封信,字跡工整,標點規(guī)范,對我們全家一一問詢。落款2016年1月17日。
郵包外的地址寫得清楚,是我家的家門。誰能知道這是老師最后一封信,過了48天,人便走了。如同趕路,行色匆匆,但安詳,周到,事事妥貼有序,脈脈癡情,聲聲囑咐,囑咐我們如何待人。睹此郵包,便止不住淚水,稼生何德!稼生何才!
2016年,天知道我們?yōu)槭裁催x擇了三月五日,由兒子楊凱駕車,全家去鄭州經七路33號去看望嘉季老師。天知道又為什么到寵物市場堵車,過了11點,車陣還穩(wěn)如止水。怕老師中午留飯,只好折回舞鋼。兩天后,田田哀哀的給她奶奶打回電話:“我去看龐奶奶了。龐爺爺就在我們堵車的那一天去世了。”三月五日,陰陽兩界,老師與我們擦肩過,去到那個世界,永訣就發(fā)生在來不及流淚的時刻,慘!不該如此慘!她奶奶把消息告訴她姑姑林杰,囑林杰別告訴我。瞞了許多天,才告訴了我。
這消息,我不敢、但也不能不告訴溫哥華的痖弦先生。嘉季老師和痖弦先生未曾謀面卻互相敬重。2014年,兩人要我給他們尋找會面機會,而我沒有做到。我為兩人悲傷。
此岸彼岸兩個人:一個從《創(chuàng)世紀》《幼獅》《聯合副刊》《聯合文學》一路走過50年,其文學版圖庶幾就是一部臺灣文學史;一個從《翻身文藝》《河南文藝》《奔流》《莽原》一路走過50年,成為共和國第一代編輯家;青鬢皓首為他人作嫁,為文學人鑄魂(趙富海語)。兩人同根、同源、同道、同守,何其相似乃爾。
至今我們只見到嘉季老師一篇《山寂》(散文選刊1987.11)。文章寫得空靈,卻因空靈而凝重;實力彌滿,從“寂”中釋放出撼人心魄的音響和動感,氣象萬千,在藝術享受中提升著我們的人品和風神。我們看到了寡言的老師胸中的丘壑。此等佳構,若能“等身”,該多么迎心啊!他早生華發(fā),編壇上一團白云,白云下,一臉和善,誨人不倦。終生精力都給了人,自己的,只此一篇,成為絕響。痖弦先生以詩名世,然而只有80來首;其余的文字,為71位作家畫家梳妝,迎候他們一一出道。
彼岸此岸兩位編輯家。編輯家必然也是教育家。兩人在兩岸給作者寫了很多很多的信,成為編者作者的情感大觀,待有心人發(fā)掘這筆人文財富和文學史料。
嘉季老師給我的信并非是一對一的“來回”信,尤其在我女兒林杰和孫女田田次第成人長大的這一段,信函電話密度更大,癡心讓她們如何做人、如何待人。林杰編出第一張小報副刊,老師喜瞇瞇地說:林杰長大了,這是她發(fā)軔之作。老師在版面上勾勾劃劃,標明許多優(yōu)點和缺點。老師對田田呵護有加,田田給龐爺爺的片紙片言和畫作,連同信封,龐爺爺就將其裝入一個牛皮紙袋里保存;田田從經七路33號院1號樓下來,龐爺爺龐奶奶緊跟后邊,告誡田田別隨便坐出租車。這情分,已是天倫之眷顧了。田田尚小,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;我為之記下這細小的事,過些年,田田就會知道龐爺爺了,歲月識人!
把以上事情告訴給痖弦先生,痖弦先生良久無聲。待他恢復了說話能力,才聽到:“老天無情……”,片刻說:“不久前我還收到龐先生特快國際專遞,寄來西南聯大的資料。”痖弦先生十分崇敬西南聯大在中國教育史上的地位,而嘉季老師又恰是西南聯大學生。兩人在兩岸經營文學的面貌又是一式兩版,如出一轍。溫哥華又一聲長嘆:“唉,老天無情!”痖弦先生把他倆終生未能謀面,歸咎在天,無意在人;而我,卻引咎自責,是我沒能為他倆會面盡心,用趙富海先生在悼念嘉季老師《人瑞在天》的總旨,是我沒能為兩位文學人鑄魂。
我心悲彌……
